>>> 中繁版書名:《最後的手稿》(馬可孛羅)
上週二,3.35pm,窗外一場突如其來的雷陣雨拖住我出門赴約。腦子才閃過這場雨何時會停的疑惑時,桌上電話響了,是原本約好3.45pm見面的人。兩個原本應在10分鐘後坐在咖啡廳碰面的人,被這場雨壞了事,於是我們索性在電話兩端聊起來。桌上時鐘和窗外雨水像是滴答雙人樂團,吵得我們說得不暢快,於是她問:「雨小了,還是出來喝杯咖啡吧?」10分鐘後,外頭還飄著雨,但我們倆已坐在只能容納十人的小咖啡館裡點好拿鐵加鹹派,繼續掛電話前的幾本書提案,聊著夏季書市裡那些出色的作品。
話間,我腦子閃過一個念頭:編輯是「書」的裁縫師,而文學經紀人就是為它尋找一位熟知它的尺寸的好裁縫,我們不怕裁縫師沒有名氣,就怕師傅的手不巧。每位編輯都是懂裁縫的裁縫師,也懂得挑布(書),但有時裁線(文案)剪錯,一塊好布(好書)有可能就毀了。
2009年IMPAC都柏林文學獎決選小說《最後的手稿》(The Archivist’s Story)有一句話,我個人很喜歡(當時坐在我對面喝咖啡的人同樣讚賞這句話,但希望做出這件事情的人不是編輯):
……我的手捧著世界文學瑰寶,但我的工作是親手銷毀它……
《最後的手稿》這本小說雖沒獲獎,卻已賣出13國語文,英美銷量不俗。故事背景發生在1939年的莫斯科。一位落魄的文學教師帕維爾迫於生計,在臭名昭彰的比揚卡監獄擔任檔案管理員。每天,有堆積成山的詩詞、小說和傳記的檔案夾送到他的桌前,但他的工作不是歸檔,而是將這些被政府當局列為有問題的手稿銷毀。
這間偏遠的比揚卡監獄是政治犯的囚禁地,陰冷、潮濕、終年不見天日。這裡四壁的灰暗色調是帕維爾的心,因他的妻子死於一場車禍,母親死於腦瘤,就連他最親近的導師也因反抗政府當局的執政被捕。帕維爾很愛讀文學,也曾是喜歡與學生討論文學的老師,但接連面對人生的挫敗,推他走向自暴自棄,拋開良知的束縛,忠於當位銷毀手稿的檔案管理員,毫無情感地燒掉每個文字,不然就是拿給鄰居捲煙。
如果帕維爾這一輩子沒有接到這項任務的話,也許若干年後,他的名字會與這座監獄一起寫進歷史,遺臭萬年。
這個任務就是帕維爾的上司派他找出手上一份匿名手稿的作者。經過多日來的調查分析,他鎖定的對象是知名小說《紅色騎兵團》的作家以撒.巴貝爾,他也是比揚卡監獄的頭號囚犯。這部小說就從帕維爾在獄中與以撒.巴貝爾的對話掀開序幕。從兩位男人的對話中,我們可以嗅到帕維爾的句句進攻,卻也可以聽到以撒.巴貝爾的層層防守;我們可以知道帕維爾讀過每一本以撒.巴貝爾的書,是他的書迷,卻也可以得知以撒.巴貝爾在監禁期間被剝奪寫作的權利,但他憑著毅力與智慧完成兩卷手稿,坐在他對面的帕維爾是唯一能拯救手稿的裁縫師。
帕維爾結束與以撒.巴貝爾的對談後,他心中沉睡已久的良知掙扎地甦醒過來,決定偷藏應該燒成灰燼的第一卷手稿,隨後再偷運出第二卷,並將這兩卷手稿藏在地下室其中一片牆的鬆動磚塊後面。帕維爾十分清楚東窗事發的嚴重後果。但這兩卷手稿燃起他面對強權不退縮的勇氣,也喚起他原本失去意義的人生。
......在陰鬱世界裡,良知和人性究竟能走多遠?......
這句話也讓我喜歡不已,不停在心中背誦好幾次。
《最後的手稿》是一個充滿懸念、勇氣和慈悲的故事。作者筆下刻畫的每一角色都散發出憂傷的氣息,每一劇情都顯露出悲傷的氛圍,但主角帕維爾的使命讓這本書擁有溫暖的核心價值──希望。它雖是畢業於密西根大學的美術碩士的特拉維斯.霍蘭德(Travis Holland)的處女作小說,但他的短篇小說早已散落在美國知名報章雜誌,並兩度榮獲紀念著名劇作家艾弗里.霍普伍德所成立的霍普伍德小說獎(Hopwood Awards),是不可多得的新生代才子。美國暢銷小說《歷史學家》作家伊莉莎白.科斯托娃也跳出來讚賞背書:「特拉維斯用一種細膩的筆觸,創造出一件稀有的藝術品,讓我們在閱讀過程中,不自覺地強化那一段歷史的回憶。」
一塊與朋友分享的書天地
想要閱讀
- • 驚悚小說暢銷天王丹‧布朗最新力作《失落的符號》── 2010年1月29日請你來解謎!1月8日預購開跑囉!(時報, 2010.01.27)
- • 《購物狂》系列作家蘇菲.金索拉早年以本名梅德琳.威克漢發表的都會小說:《意外之侶》(馥林, 2010.01.22)
- •《蘋果橘子經濟學》繼續用經濟學解剖事物的隱藏面:《超爆蘋果橘子經濟學》(時報, 2010.01.11)
- •《好書情報》雜誌說:「這是只有史蒂芬金大師才寫得出來的小說」:《失眠》(皇冠, 2010.01.11)
- • 西恩‧史蒂文森是先天成骨不全症患者的字典裡永遠沒有「可是」兩字,而我們身為健全人為什麼坐在「可是論」上裹足不前呢?現在就起身,從一個小小的改變做起:《拒絕可是的人生》(臉譜, 2009.12.29)
- • 巴菲特、馬友友、伍茲,甚至莫札特,研究證明,這些「天才」和我們不一樣之處,在於他們長期、有方向地進行「刻意練習」自我琢磨:《我比別人更認真》(天下文化,2009.12.28)
- • 電子郵件如何幫你拿訂單、受重用、結人脈?:《天哪!我居然CC給他》(大是, 2009.12.28)
- • 不僅讀心,同時影響別人下決定:《看人看到骨子裡》(方智, 2009.12.24)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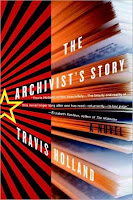

沒有留言:
張貼留言